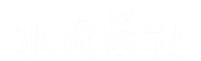Advertisements

(圖片:阿清)
[詩學評論展]
一個人的“朝圣”路
——讀劉志清詩集《歡快的小鳥》
束旭燕
(塔里木大學2020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
[摘要]新疆詩人劉志清在詩集《歡快的小鳥》中所構建的精神世界,涵蓋了詩人對個人生命歷程的書寫。以高揚的筆調,回顧了兵團的發展歷程與新時代下的兵團面貌,同時在精神的自足中完成了生命的詩意蛻變。
關鍵詞: 生命歷程;兵團精神;詩意蛻變
兵團詩人劉志清的文藝創作開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是詩歌熱潮席卷而來的時代。詩人說:“那時的我成為詩神繆斯狂熱的追捧者,并從此開始了三十年詩意放蕩的人生軌跡。”[1] 在詩集《歡快的小鳥》中,劉志清所構建的精神世界不僅是詩人自身情感的詩意表達,更完成了詩人生命的詩意蛻變。本文對詩集《歡快的小鳥》將從作者生命歷程的記錄、兵團精神的高歌、生命的詩意蛻變三個方面,解讀詩人劉志清是如何在詩神繆斯的指引下,完成精神世界的實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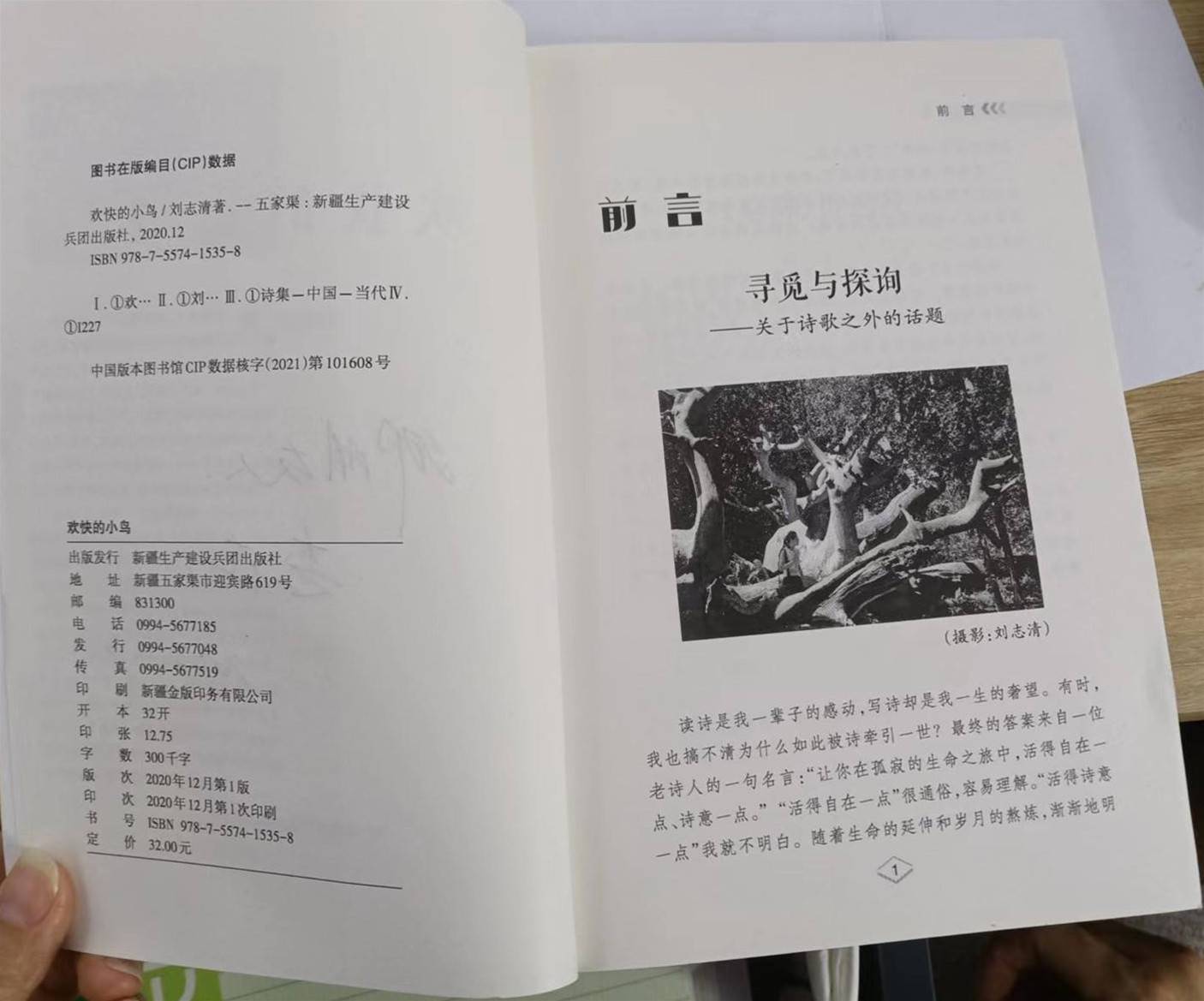
(圖片:阿清)
一、生命歷程的記錄
詩歌并不是嚴密邏輯下理性思維的產物,而是人類情感在某一事物上的投射與象征式表達。對兵團詩人劉志清而言,寫詩的目的在于探尋和尋覓詩的本真。詩歌貫穿著劉志清的一生,他將自己對生命的體驗與感悟凝結在詩句中,詩歌成為詩人成長歷程的映射。
回首兒時“那是一個沒有欲望的曠野/那是一個沒有貪婪的仙境//鄉村,是我童年年畫的背景/田塍,草根饋贈我生命的甜蜜/烤紅薯是我最奢侈的干糧/野果子是花不完的私房錢//紅紅的光腳丫子/在魚塘中泡得像個皇帝的玉璽/彎彎曲曲的田塍路上/歪歪斜斜地發布大地的諭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童年,是搖籃的夢曲》)。在劉志清的回憶里,兒時的土地“是一個沒有貪婪和欲望的仙境”,土地上充滿了天然的“玩具”——草根、烤紅薯、野果子和被魚塘泡得發脹的紅腳丫,充滿歡樂與想象力的童年成為詩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兒時的“我”肆意奔跑在家鄉豐碩的土地上,土地的滋養與幼年美好的回憶,讓劉志清始終保有一份孩童般的天真。正如詩集序言中肖濤教授所說:“我驚異于這個自稱‘我是森林中一只歡快的小鳥’的男人筆耕三十年的厚重與深邃,遠不是表象所見到的那個說話語速較快,帶有湖湘口音,在人群中安靜時看不到人,熱鬧時帶著孩童般的笑可以說個沒完的劉志清”[2]。童年對每一個人的影響都是無法抹去的,尤其是對一個詩人來說。劉志清企圖將人生的歷程與行走途中的感悟用詩意的表達傳遞給這片土地,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讀詩的人,更加充分地認識到詩人的寫作境遇,從而讀懂詩歌,進而讀懂土地上的人民。
在童年美好的部分之外,劉志清寫到“ 從小銘刻在夢中的那份天性/就是鄉村孩子們的游戲/男孩骨髓中總有一種殺氣/想要征服世界分賞成就/望子成龍是每個做父母的心愿/而天下的龍又有幾條?”(《童年,是搖籃的夢曲》)作者此時的情感從對兒時美好生活的懷念轉至對社會問題的思索,劉志清認為孩童的天性不應被扼殺在成人世界的競爭中,只有保留一份童真與自由,才能使他們在向成人世界的過渡中不被世俗的名利與欲望淹沒。
詩人自1993年大學畢業后來到一師阿拉爾市廣播電視臺(現在是第一阿拉爾市融媒體中心)工作至今 ,“記者”一職,曾經 是劉志清 入職歲月的片段歷程,一頭扎進去也有二十年的生命閱歷。寫詩是心靈的驅動,并不是他謀生的手段,而是追求世界本真的一種方式。劉志清用自己的人生踐行著詩意地棲居,因而我們可以說:劉志清的寫作是由心而發。現代詩歌應當回歸純粹、尊重本心,而非在現代化的急遽進程下成為他者的附庸,這也是現代作家在創作中應當極力避免的。華茲華斯曾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與表達”[3]。正是在這樣的創作前提下,詩歌才能真正成為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橋梁,實現自身的價值,達成使命的轉換。
(圖片:阿清)
童年的經歷對劉志精神世界的塑造有著極大的影響。在《鄉間那個月亮》一詩中,詩人的懷念對象從個人變為他人——“鄉間那個月亮總是那么慘白/像分娩的村姑失血過多的臉//父母都外出打工了/留守的孩子沒人管了/池塘,山坳都是危險地帶/像埋著定時炸彈/隨時威脅著鄉間的安寧//月夜,一個失去孩子的女人/在月光下四處夢游/發出凄婉的哭喊/披頭散發的頭顱/晃動貧血的臉/好似月亮滾落到人間……招魂的時候/夢游的身影/總是裸奔在漆黑的夜間/月亮是她唯一的聽眾”。作者將鄉間的月亮比喻為“分娩的村姑失血過多的臉”,奠定悲涼的基調。與兒時的“玩具”不同,鄉間的月亮是象征苦難的月亮,苦月亮的慘白給兒時的“我”留下了懵懂而深刻的印象。鄉村生活給予孩童自由的背后,是親情的缺失與經濟發展的失衡。每當“我”凝望起兒時的月亮,那個失去孩子的女人慘白的臉如同夢魘,粗魯地闖進“我”童年的美夢。那時的劉志清似乎已經認識到:這個世界并非一個孩童所能輕易揣測明白的。像城南胡同里的英子一樣,“我”渴望學會長大,學會用大人的眼光去探究這個世界。劉志清將自己置身于孩童的視角,企圖用平靜的敘事將讀者拉進那個“慘白的月夜所照射的世界”中去。在這樣的視角下,詩歌完成了“小我”向“大我”的轉變,詩人的詩意世界向著更深處耕耘。
在生命歷程的推進中,劉志清筆下的描寫對象逐漸豐富起來。從對自身從事的職業關照到對白衣天使的贊頌——“護士,一個平凡的崗位/每天與死神擦肩較勁/你像一個家庭中的母親/時刻把每一位成員都細心呵 護/任何病毒的偷襲都難買通你的心靈”(《“白衣天使”的贊歌》)。在疫情背景下,護士這個職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超負荷的工作加上日夜顛倒的作息在病魔面前顯得那么徒勞,然而在望向那無數雙充滿渴求的雙眼時,她們依然堅守著最初的信念、她們依然選擇裹挾著洪流艱難前行。詩人深知幸福是如此來之不易,因此在面對記者這個再熟悉不過的職業時,他必須更加仔細,才能對得起前輩們用生命換來的今天——“中國記者節/一個不同于任何節日的節日/一個并非鋪張的節日/誕生于世紀之交的光輝歲月/它凝固著幾代中國新聞工作者不屈的靈魂”(《記者,一個閃光的職業》)。如果說護士是生命的守護神,那么新聞工作者便是生命的洞見者,他們用一篇篇凝結著血淚的稿件向世人訴說著人性的幽微與世界的復雜。這個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只有透過多面的分析與考察才能勘透那黑幕之下的真實。
豐富的人生閱歷與多重社會身份使劉志清在詩歌創作中既能精確把握個人“小我”的情感,也能以大情懷悲憫人間,為散發著微光的普通人作詩。回首過去,劉志清所收獲的遠遠多于所經歷的,在生命的修行中,因為有了詩歌的陪伴,路途顯得如此平坦。這也啟發我們,在只有一次的生命體驗中,過程遠比結果重要。因此,不妨活得大膽一些、詩意一些,只有這樣才能無愧于心,不虛此行。

(圖片:阿清)
二、兵團精神的高歌
新疆古稱西域,身處祖國西北部,緊鄰歐亞國家,深受多元文化影響,在中國各民族文化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許多曾經踏足新疆詩歌領域的文人都深受新疆地域文化的影響。兵團作為一塊特殊的土地,雖緊鄰沙洲戈壁,少有綠植,但這里出產的棉花和文人風骨卻一點兒都不亞于富饒之鄉。前者仰賴于邊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后者則根植于西域新疆的千年歷史文化。時至今日,這片占據“共和國六分之一”的土地仍然不斷挖掘著、創新著、更迭著內部自我的精神價值。兵團詩人劉志清常年工作、生活于一師阿拉爾市,他感受著這片貧瘠的土地帶給他的一切:連綿的瀚海,曲折的河流、守疆的戰士、 勞作的人民……對這一切的書寫,都是凝結于土地之上的兵團精神的寫照。
站在兵團的土地上,“當我用發顫的雙手/捧起熱血的沃土/捧起的是祖輩們/換做泥土的骨灰/”,兵團是一個光榮的稱號,亦是一個沉重的稱號。如同詩人所說:那片如今的沃土是祖輩們化作泥土的骨灰。劉志清想到祖輩們是如何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土地,那段光輝歲月如同電影畫面般一幕幕出現在眼前,作為土地的兒女,“面對南泥灣精神的續篇/我的靈魂在大漠廣博的舞臺/如紅柳落英繽紛般隨風翩躚/墓碑的光影銘刻紅色的經典”。如果沒有那些因緣際會,劉志清對新疆、對兵團的印象或許只會停留在山水人情之中。或許是前世有緣,在劉志清的詩歌中,我們看到的是二者之間的雙向選擇。邊疆給予他糧食和土地,他贈予土地詩歌與熱愛。面對“南泥灣精神的續篇”,劉志清以筆墨延續開墾的精神,并坦言“無論你轉業處何方怎么稱謂/特殊奉獻曾扛起雪域的脊梁”(《兵團,飄揚的旗幟》),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盡情流淌在筆墨之中。在劉志清筆下,兵團的價值與意義并不是相對于新疆、相對于中國而言的,而是中華文明在經過不斷的肢解與重組下強大生命力的體現。
“他們像崗樓上的哨兵/守望著天邊的位置/他們像左宗棠帶來的江南柳枝/插在戈壁灘上染綠鹽堿的家園……綠色是他們/高舉的旗幟/迎風飄揚”(《農場人家》),基辛格在《論中國》中說:“中國人總是被他們之中最勇敢的人保護得很好”[4]。在劉志清筆下,勇于自我犧牲的邊疆戰士、兢兢業業的兵團人民是中國人里最勇敢的人;在新疆人民眼里,放棄現代都市優渥、便利的生活,輾轉扎根邊疆、書寫邊疆的人亦是新時代下最勇敢的人。在兵團的養育下,劉志清的詩歌種子已然深深融入兵團的泥土中——“兵團的歲月/是荒原的歲月/是戈壁灘與鹽堿地上/蘆葦花長出來的歲月/是古墓與駝鈴聲/碾壓出來的歲月/是日照時長反差懸殊/綻開銀色棉海的歲月/是大漠落日/向西天燃燒的歲月”(《彎月脖子下掛著的星星》農場系列組詩),劉志清將兵團的開墾歲月、歷史遺跡、農作面貌、大漠風情以浪漫的抒情筆調濃縮在一首詩中。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座特殊的城市平靜地講述著它的前世今生:那批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曾經是一個團、一個師、一個分隊,他們靠著頑強的毅力跨越幾百公里的沙漠瀚海。后來,他們成了一段被頻頻回首的歲月。他們子孫延續著祖輩的信仰,世代堅守在這里,尋覓著歷史的痕跡,不斷鑄造著兵團新的面貌。
歷史的發展離不開人的塑造。劉志清深知:沒有人民,就沒有土地的今天。兵團人民對西部土地的貢獻不同于北京深圳人民對現代化所做的貢獻,兵團人民的奉獻是自我犧牲式的、是具有歷史創造性的貢獻,是中國精神的西部體現。因此在劉志清的詩歌世界中,他將自己對于美的定義實踐在了兵團的土地上。多年的記者生涯與寫作經歷,使劉志清看到生命歸于本真之后的模樣——站在大漠廣闊的土地上,“我”看見“一間紅柳夾墻的泥屋/點綴著曠野的風景”,如果能止步于此,“我”只愿“養兩三頭牛四五只羊/喂七八只雞種八九棵樹/在洪水浸泡的土地上/撒一些麥種播悠遠的四季”,“我”只愿不斷記錄“輪回的歲月,看著它們重復一個永恒的主題——生命”(《大漠印象》)。在寒來暑往中,將人世間的秋收冬藏盡收眼底。在劉志清的筆下,我們似乎能透過詩歌看到一個看透世事卻不諳世事、只鐘情于詩歌的朝圣者。詩人行走在西部荒涼的土地上,開墾出了自己的詩歌世界。三十年的詩歌耕耘,兵團的土地接納著他,審視著他,更創造著他。由此,這場精神聚變在兵團精神日漸成熟的今天創造著屬于它的朝圣。
三、生命的詩意蛻變
從時間維度上看,詩集《歡快的小鳥》跨越了詩人的青年至中年時期。不知是來到新疆的第幾個年頭,詩人對生命流逝的感覺越來越清晰。或許是父親頭上刺眼的白發、或許是妻子臉上新增的皺紋、或許是女兒對父親一句溫暖的問候,讓劉志清開始對“生命”話題的思考與寫作。
《墓碑》是劉志清詩歌創作道路上里程碑式的存在,詩中飽含對父親的追思與生命的啟迪。父親的離去帶走了一個男孩兒不曾言說的信仰——“父親離去三載/墓碑開始與我對話/我無法破譯它的文字/只能用心神用領悟/某月某日對父親的深深歉意//走來走去生生死死/令人柔腸百折多少回在夢中/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墓碑,您是唯一生者對死者/訴說悲歡離合的聽眾”。生命成長中的羈絆在父親離去三載后化為縷縷情絲。三年后,“我”終于理解為人父的艱難,對父親生前的誤解與故去的悲慟夾雜著無限思念最終化為一份歉意與理解。在詩歌的世界里,詩人完成了生命的蛻變。劉志清將自己對親人的情感以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使之成為雋永而無限的存在。他對精神世界的探索從對童年的回憶到對他人存在的思考,從對祖輩的緬懷到對生命意義的追問,皆是詩人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與人生哲理的詩意寫照。讀者的閱讀體驗跟隨著詩人的視角,感受著詩人的見聞與喜怒。
“這些年,在繆斯的佛光下,我尋覓與探尋詩的本真,在人生的掙扎中挖掘關于詩歌之外的話題”[5]。從悠悠長河到雪域高原,從人文風情到家國抱負,西域的變遷歲月貫穿詩人的成長歷程。正如詩人自己所說:“讀詩是我一輩子的感動,寫詩卻是我一生的奢望。”詩歌不能表達的部分,正是“我”將用一生去踐行的部分。扎根邊疆的這些年,飲天山水,頌大漠情,在劉志清筆下,天山成為圣潔女神的化身——“半個世紀的風雨雷電/將你錘煉成為神話隊伍中的圣母/你們在神話般生命的火焰中/鳳凰涅槃。 ”中華文明是歷經過坎坷與捶打的文明,西域邊疆是經受過鐵蹄碾壓的土地,磨難過后,他們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包容。或許,詩人也曾在某個深夜懷念著家鄉的月亮,筆下生出濃濃鄉情,但此時此刻,這里的一切又讓他產生無限眷戀,或許詩人早已了然:鳥兒的歡快,只有千里跋涉過的人才懂得。其實,劉志清早已將自己看作兵團的一分子,對河山的贊頌,正是他對祖國母親深情地寄語——“在大漠廣博的靈魂深處/有一根臍帶連著母親的子宮/母親那迷情幽遠的圣殿/就是我生命的源頭//在大漠廣博的靈魂深處/有一位老人和我不期而遇/他以先賢的智慧/大漠的胸襟/用愛的暖流滋潤綠洲的生命家園”(《塔里木河——我的母親河》)。河流滋潤著土地,使戈壁成為綠洲,它像臍帶連接著文明的交流。正如詩歌之于詩人,它像智慧的化身,用文字連接著文明的存續。“詩從何處來?走向何處去?”也許答案就藏詩里。
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跋涉在人性荒原上的俗世凡人,對藝術創作者而言,小說或散文題材顯然更為大眾所接受,然而對兵團詩人劉志清來說,既然選擇了久駐西北,詩歌便成了他一生的宿命。如果說邊疆是他的第二故鄉,那么詩歌便讓這個看似無根的漂泊游子艱深地扎進了西北的戈壁之中。劉志清坦言:詩歌創作是為了讓生命包容詩的存在,讓詩像血漿一樣凝固在骨髓之中。在新疆生活的匆匆幾十載,使詩人從一個青蔥少年成長為大漠中自由地行吟詩人。他一路行走一路歌唱,任憑歲月從詩句中溜走,懷揣著對生命的深刻思考和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無限眷戀,劉志清完成了自己關于生命的詩意蛻變。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他將會無限接近于生命的本真,完成自己詩意世界的創造。
(圖片:謝君鵬)
“我是森林中一只歡快的小鳥,在空氣與白云中自由地飛翔。我想飛就飛,想唱就唱,想棲就棲,想瘋就瘋,想吼就吼……我不被任何約束”[6]。這是詩人內心的獨白,也是筆者讀詩的深刻體驗。當讀者全身心投入詩歌之中,閱讀的已然不是詩歌,而是詩中所映射出的自己。跳躍的思想,無序的語言、看似隨意拼湊又合乎情理的邏輯、眾多意象組成的無限遐思、不知歸處的落筆、自由靈魂訴說著無限可能。無論是詩人自己還是讀者,似乎都能在這場文字博弈中找到生存之外的另一種答案,由此擺脫困頓,創造無限可能。好的詩歌能夠超越自身給予我們豐富的情感價值與精神依托,也許這就是寫詩之于作者與讀詩之于讀者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2][5]劉志清.歡快的小鳥·后記[M].五家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20(12):370、4-5、2、371.本文所引用的詩句皆出自該詩集。
[3]劉端若.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G].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6.
[4]亨利·基辛格.論中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7)
[作者簡介] 束旭燕,為塔里木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大三學生,曾多次獲得專業獎學金。熱愛文學與生活,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認真清醒的人。此文獲得新疆文聯、新疆大學和新疆教育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文化潤疆沃天山——首屆新疆高校師生文藝評論大賽”本專科生組優秀獎。
指導教師: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胡昌平教授。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