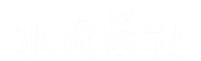Advertisements
1997年,時任日立CEO的牧本次雄首次提出“數字游民(Digital Nomads)”的概念,用來形容依靠互聯網工具而擺脫了地域限制的工作者。據統計,全球有約3500萬數字游民,聚集在巴厘島、國外清邁等地。
不久前,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浙江湖州的安吉溪龍鄉也有個數字游民公社。在媒體過往的描述中,一群年輕人不用坐班,他們聚集在美麗的鄉村社區,自由、熱情、沒有約束。
安吉,縣名取自《詩經》“安且吉兮”,三面環山,一面開闊,竹海依依,是白茶之鄉。西苕溪穿境而過,溫暖濕潤。這一切,都讓人心向往之。
于是,帶著好奇,作者梁靜怡踏上了她的安吉之旅。然而,我們很快發現,這里并不僅僅是一個詩和遠方的故事。
進入溪龍鄉
大學畢業后,我再也沒住過集體宿舍,直到我來到安吉數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以下簡稱“DNA”)。六人間很便宜,一周僅需180元。條件樸實無華,房間十幾平米,一眼到底,三張上下鋪床,行李箱堆在過道,衛浴室內滿滿當當。
蜷著腰,我爬上角落的上鋪,第一夜,不時被手機震動聲吵醒。我不斷告訴自己,房價僅25元一晚,沒什么不能適應的。
次日,當暖烘烘的太陽光照入那一刻,昨晚的不悅似乎全被沖散。DNA的全貌在陽光下顯露,這里背靠茶園,遠山黛影。幾只山羊“咩、咩”叫著,在球場漫步。

球場旁,兩棟白色的主體建筑由廢棄的竹木制品廠改造而成。其中一棟是磨砂外殼竹木吊頂,有寬敞的階梯辦公區、娛樂區、宿舍和洗衣房。從中穿堂而過,則是竹林掩蓋的集裝箱住宿區域。另一棟建筑是公共食堂、健身房和KTV室,小溪從窗邊躍過。
太陽一點點爬升,正好照在房頂,上面立著幾個大字,“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起來”。標語下面,幾位數字游民曬著太陽,捧著電腦,在田邊工作。他們在一份小報上這樣介紹自己,“一種被新時代賦予可能性的全新生活方式”。
“原來的生活不好嗎?”我問阿綠。我在階梯辦公區注意到阿綠,她今年26歲,剛從一家互聯網大廠離職。在DNA,她總是裹著棕色搖粒絨大睡衣,一邊看視頻,一邊奮筆疾書做筆記。
如果不辭職,“心理會難以接受”,阿綠說。她原本在銷售崗,每天從早上8點半工作到晚上11點,回到家累得只想休息。目睹身邊年紀輕輕的同事得了病癥,于是每周末她都去報復性健身,有次練拳擊練到吐,吐完接著練。只有這樣,她心里才會恢復一點安全感,“好像我過得比較健康。”
公司部門的狼性文化不斷刺激著阿綠的購物欲望。沖業績的日子里,若沒有達到原定目標,老板會命令她馬上去買個奢侈品包,以此激發斗志。心理壓力大時,她也會一次性買20件衣服,租來的小房間都被堆滿了。
在原公司,她很快有資格申請數十萬元的無息貸款買房。可她看到公司里的中年人,有了房貸和孩子,“就感覺被套上了,”車轱轆只能轉下去。最終她帶著焦慮辭職,來到了DNA。
阿綠, 26歲,剛從一家互聯網大廠離職。
在這里,像阿綠這樣從體制和大廠逃離的故事并不新鮮:一位譯者逃離了“把思維像漿糊一樣搗碎的坐班機器”;一位產品經理逃離了“后廠村的社交荒漠”;一位銀行職員逃離了“得靠聯系才能爬升的職業路徑”……
安吉宜居,氣候溫暖濕潤,太平天國年間,為躲避戰亂,河南、江蘇、湖南一帶的百姓遷徙至此定居。現在,有一群年輕人告別城市,遠離“卷”的生活,來到這里。他們在這里從事設計、Web3、翻譯等遠程工作,或純粹地親近鄉野,治愈自己。
5公里外是連片的茶山,游民們相約早上8點從DNA跑步出發,沿路經過鄉間小道、村莊,到達山頂時,晨霧未散,米白山茶花的清香飄來。飲著熱茶,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綠,一位游民把云霧背后一間閑置的小屋租下,打算將里面裝滿詩歌。
溪水在竹林間潺潺。一位游民脫口而出,“我真的可以這么幸福嗎?”
然而,我很快發現,故事遠沒有這么簡單。
遇到金主
一天,我和游民們正在鄉間路上走著。一輛寫著“豪華夢想支援小組”的小巴車突然停下來,一位身寬體胖的中年男士探出頭,問我們要不要搭順風車。
他是DNA的主理人老許,今年54歲,杭州人,此前從策劃公司辭職全世界旅行,后定居大理。
老許目睹了大理社區的形成過程:上世紀80年代,外國嬉皮士在那里聚集,慢慢生長出西餐廳、披薩店和咖啡館,吸引了后來的背包客和游客,任何怪異的、小眾的興趣都能找到同伴,朋友們總在書店或咖啡館偶遇。老許也和書店老板阿德成了好朋友。
他們形成了關于社區生態的一套理論,其中的關鍵是,社區形成初起要有一批種子人群,“80年代的大理,老外就是(種子人群)。”阿德說,“就像珊瑚礁的生態形成過程,先有珊瑚,再有小魚小蝦,然后再吸引更多的生物過來。”
老許和阿德一直夢想著能夠在其他地方復制大理社區,讓年輕和自由的故事再次生發,終于,他們的夢想在安吉實現了。

老許, DNA主理人。
在DNA社區生活是一種奇妙的體驗。去年3月28日晚,階梯辦公室里坐滿了人,一位酒吧老板分享了“如何上脫口秀大會”。像這樣的活動在DNA常常出現,數字游民們自發地組織唱歌、吃火鍋、分享會。可身為主理人的老許和阿德,卻常常隱身在微信群中,很少發起活動。這里幾乎沒有私人空間,四處都是連門都沒有的公共空間,即使密閉空間也有通透的大落地窗。
老許稱刻意為之:房間故意設計得通透,“如果是實墻,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則不會加入(聚集)。”隱身是因為老許拒絕成為領袖,“去中心化”。因為如果有領袖,社區就會存在隸屬聯系,存在“命令”和“不自由”。“我們要創造的環境是讓大家覺得輕松。”
我確實無時無刻不在和游民朋友們偶遇,圍繞DNA 1公里的生活基礎設施極其便利。騎著小電驢5分鐘即可到安吉創意設計中心工作,那有免費的圖書館、設計工坊。旁邊就是食堂,我和游民們總在這里約飯。
老許的敘述充滿了理想主義,可我內心滿是疑惑。DNA的廠房改造花了2000萬,即使DNA住滿人,每月的收入6-7萬,只能剛剛覆蓋運營成本,更別說還有圍繞DNA的其他配套設施。我在食堂吃了一頓牛肚炒蒜苔、清蒸小黃魚、蒸蛋、咸肉白菜和排骨湯,DNA會員打5折,一共只花費26元。誰在為此買單?
老許說,他的雇主,以及眼前這一切的背后金主是一家房地產公司,上海愛家集團((以下簡稱“愛家集團”)。
此前,我印象中的房地產老板都是中老年男人,微胖,腦袋發亮。因此,當李彥漪出現時,我吃了一驚。1992年出生的她染著紫色頭發、化著眼影,雙手抱著小狗,十個指甲都涂了不同顏色。
李彥漪,愛家集團二代掌門人。
李彥漪是愛家集團二代掌門人。2023年,愛家集團與浙江安吉溪龍鄉政府簽約“我們·安吉白茶小鎮”鄉村振興綜合體開發項目,打造溪龍全域鄉村田園旅游綜合體。這是她接班后主導的第一個項目。
李彥漪的父親在上世紀末創辦了愛家集團,躋身我們房地產百強企業。李彥漪14歲就出去讀書,一路讀到博士。讀書之余,她都在旅游,“那個時候我覺得,工作就是為了賺錢,我們家不需要我賺錢,所以我不需要工作。”
2017年,平常寡言的父親突然打來電話。回來后,她才知道,父親的身體不太好了,給她留下上百億的盤子。剛接班時,我們的房地產行業仍在高歌猛進,跑馬圈地,走高杠桿、高周轉模式。隨著房地產調控新規的變化,高周轉錢生錢的房地產神話破滅了。
看著許多地產百強榜內的公司突然沒了,李彥漪極度焦慮,她說自己突然有了白發。房地產需要新的敘事了。
以前在國外讀書時,李彥漪去過歐洲、國外的一些鄉村,那里干凈、有趣,有很多生活體驗項目,給她留下美好印象。2018年安吉溪龍鄉想引進全域開發,李彥漪看到安吉溪龍鄉連片的茶山,覺得與自己曾去過的國外鄉村很像,她拿下了這個項目。“我當時很真實的想法,大不了就抄一個。”
她的想法并不被業內其他大佬們認可,因為此前已有諸多房地產公司躬身入局特色小鎮,又頻頻敗北。一位大佬譏諷道,年輕人有夢想還是好的。他們覺得她無非是一個任性的年輕女孩。
李彥漪恰恰覺得自己與他們不同。這些人過中年的老板們還停留在當年圈地賣房的模式,“沒有經歷過國外鄉村的美好生活,平時天天就是應酬、工作,你讓一群沒有生活的人去創造美好生活,這是一個偽命題。”李彥漪說。
可真的操盤起來,并不容易。整個項目面積32平方公里,相當于再造一個澳門。安吉有白茶,李彥漪曾去過的國外靜岡和宇治有綠茶,于是,她帶著團隊再次去考察,卻發現“抄一個”的想法過于天真。國外的農場主有很強的做衍生品的欲望,體驗式的觀光旅游意識很時尚。
但安吉的基礎設施和氛圍遠遠不夠。資料顯示,當時溪龍鄉GDP總值中,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占比高達87%左右,而以旅游業、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占比只有約1%。游客太少了。
一個用7種苔蘚制作的沙盤上,展示出了李彥漪心目中安吉白茶原小鎮的藍圖:這里將會有公園、療養中心、花園營地、2023市集,還有上萬套房產,可作民宿、酒店和住宅。
她和團隊希望,最終吸引來安吉每年2800萬人次游客,在此停留2-7天,每天花費約2000元,還有大量客戶來此購買度假和商業房產,房產價格從200萬到上千萬。
可他們也很清楚,這些設想中的游客和業主只會在安吉開發完善了,人氣和名聲起來后才會過來,“這些人都是吃勝利的果實的,不會陪你走最開始那幾年的路。”
團隊在全我們尋找,誰會是早期最容易遷移到小鎮的人,一路尋找,在大理遇到了老許和阿德,被他們的社區理論吸引了。無論是安吉溪龍鄉,還是老許阿德的社區夢想,都需要最初的種子用戶。相比于一家三口搬遷需要突破層層困難,憑借單身、自由、移動成本低——數字游民被選中了。
景觀
愛家集團副總裁杜一飛帶我走進金葉子中心,售樓沙盤周圍,一切營造鄉村美好的氛圍鋪面而來:麥稈做的沙發和禮盒;戴上耳機能聽到安吉西苕溪風吹稻田、樹上蟬鳴、夜里蛙叫;盒子里有很多五彩小卡片,隨意抽一張,是一首詩:
如果塵世把你遺忘,
且對寂靜的大地說:我在奔流,
對迅疾的流水說:我在停留。
——里爾克
游民們也是鄉村美好氛圍的一部分。方圓1公里,游民們偶遇,點頭微笑,進行有趣、輕松的社交,整片土地煥發著自由、友善的氣息。這正是杜一飛想要的,在他看來,數字游民自由、美好的生活氛圍,會吸引“每一個心中還有浪漫主義的人”。
他和李彥漪潛在DNA的游民群里,把數字游民當成觀察樣本,他們邀請游民們品酒,觀察他們如何選咖啡,從而淘汰那些不受歡迎的產品。“雖然消費力不太行,但是他們愛生活,所以說很容易去觀察去看反應。”

杜一飛,愛家集團副總裁
浪漫主義的人還未至,但一撥撥背著人才引進指標KPI的地方干部已到。3月25日,棕色大巴拉來了幾大車的政府官員,DNA的籃球場都停滿了。老許前方帶路,高喊“這邊走——”七十多位西裝革履的干部們像看新物種一樣,打量著這些游民。
不久前,湖州市市委領導陳浩參觀了DNA,給這里定性為“把更多具有高學歷、高收入、高專業技能的‘三高’人才吸引到鄉村來”的平臺。一時間,各鄉縣干部組織前來參觀,熙熙攘攘。
我見到了一位來DNA參觀的干部,直言面對“蘇州新規、上海新規、深圳新規”,安吉幾乎沒有競爭力。她渴求地望著老許,“許總,有合適的年輕的資源嗎?”
“當然有資源”,老許搬出他的社區生態理論——年輕人們被這里的生活氛圍吸引,建立友誼和紐帶,停留更長時間。當人群達到了一定規模,總會有人愿意在這開一家店,有了生意就不走了,就不再是游民。這些人也會吸引來自己的朋友,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里,留下,社區就在不斷生長。
官員們的考量則更直接和“實在”。假如他們也引進了數字游民,只有這些年輕人在當地交上社保,他們才能完成考核指標。老許直言,“種子生根、發芽、開花,自然有結果的那一天,讓年輕人愛上這里就不能急。”
游民們也覺得矛盾,“我們數字游民本身就不是說要固定在哪里,怎么可能在當地交社保呢?”
3月31日,我和那位干部通了一次電話。身為基層官員,她感到有些束手無措。安吉只是個小縣城,高科技企業不多,但近幾年各鄉鎮有青年博士引進的任務,“說難聽點,老年博士你能把他引到安吉來養著都很難,你還想要40歲以下的青年博士?”
那晚,她輾轉難眠,因為31日過完,2023年新的人才引進KPI又來了。她還在努力尋找兼顧考核和吸引年輕人來鄉村的兩全之策。
游民們也成為了媒體關注的焦點。一份運營人員的媒體報道簡報顯示,DNA成立剛一年,已有20家媒體對DNA進行報道。在我入住期間,就有至少4波媒體撲入。
3月8日,一位數字游民正工作著,一位電視臺記者猛地塞來話筒要采訪,她感到被冒犯了,“就像風景區被開發一樣,我們已經是屬于被過度采伐的。”我突然意識到,我的到來,對他們也是一種打擾。
當日,一家省內新聞媒體來訪,臨時拿來一份風景區的策劃方案,說要讓搞設計的年輕人們集思廣益,建設鄉村。為了畫面好看,他們征用了二樓平時根本不會有人開會的KTV室。
那天下午,大多數游民去山上放生烏龜了。為了配合媒體,老許拉來幾個原本在品咖啡的年輕人,坐在二樓的沙發上,看策劃,提問題。我從旁觀察,發現記者并沒有真的記錄游民們說了什么,他們只是想拍一些畫面。
“我們是籠子里的動物,被觀賞著。”數字游民也很清楚,自己在鄉村成為了一種景觀。
飛地
沿DNA往外走,我看到四處都在破土動工,挖掘機聲聲入耳,馬路上塵土飛揚。溪龍鄉正處于劇變的前夕。
已經被開發的地方,和傳統的我們鄉村面貌相去甚遠。新的咖啡店和可麗餅店開業了,賣貓王三明治和黑松露熏肉蘑菇蕎麥可麗餅。杜一飛曾在上海網紅打卡地安福路生活了13年,那里紅起來的第一家店就是可麗餅店。他對溪龍鄉的未來,也有著“洋氣”“法式慢生活”的期待。
露營鄉村風的咖啡店外支起帳篷,店內播放黑膠唱片,服務員穿得像西部牛仔,游民們面帶微笑地喝著咖啡。一位前來休假的藝術家說,這里的人都好像NPC,穿著戲服,還有氣氛組擔當,讓她想起國外時光。
這些正改變著溪龍鄉。我問李彥漪,有沒有人說過,你們在復制西方的鄉鎮,或者城里的小資生活,讓我們鄉村失去原有的生態?一個數字游民也說,如果城市人到了鄉村,“還是早上起來要喝一杯咖啡,那你出來干嘛?”
李彥漪說,“你說什么東西是只屬于鄉村,或者只屬于城市的,它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
1982年,安吉縣林科所的科研人員進行茶樹資源普查時,相傳在天荒坪鎮大溪村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上,發現了一株長著玉白色芽葉的千年古茶樹。科研人員據此研發出“白葉1號”。白茶無愛繁育,僅需一片葉子,最終能長出一片茶山,安吉也成了白茶之鄉。
來安吉之前,我曾想象,這些外來的數字游民是否會成為新的一片葉子,和本地村民發生某種互動,進而造成某些改變,但我好像到來得太早。他們好似生活在兩個時區。晚上9點,年輕的游民們熬夜看世界杯時,當地村民早已入睡。白茶街空蕩蕩的,偶有時尚的香柚從樹上掉落。
DNA對面是一家海綿廠,院子里停著奔馳和瑪莎拉蒂,看門的是老板的老父親,他無法走進DNA,只是有時在外面探幾眼,看到年輕人不上班,他問我:“你們是不是在對面啃老?”
DNA和一些公共空間只對數字游民會員時尚,像是鄉村的飛地。幾位村民說,自己曾好奇想走入,但被保安擋住了,“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老許解釋,不時尚是擔心游民們財物被偷。樹下小白屋雖叫村民食堂,但普通村民得原價消費,“我們想去吃,拿你們的卡才能打五折。”一位村民說。
實際上,村民們也并不真的關心DNA的世界里發生了什么,他們更在意拆遷款到手多少和白茶行情。2023年因為情,經銷商進不來,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茶葉囤積。3月正是茶苗上市的季節,今年的茶苗是2毛一棵,三腳蹦拉著一車一車的茶苗往村外送。
數字游民社區之外,溪龍鄉的村民們過著富足而規律的生活。年輕人去徐村灣紗線、家具廠打工,老人和小孩在家里照顧茶山。一年只種一季白茶。每年清明前后,白茶街上擠滿了各地茶客和經銷商。繁忙過后,則是日常維護茶山的悠閑日子。

直到游民們帶我去附近老梅溪認識了開飯店的“小姨”,我才發現兩個世界間敞開了一些微小的裂縫。
小姨50多歲,短發齊耳,身材前掛著一塊金佛。她一生坎坷,分手后獨自拉扯兒女長大,號稱自己已經“看透婚姻”,把婚姻形容成“地獄”,可仍舊希望自己的女兒能走進婚姻。
一位游民女生說,小姨讓自己想起家鄉貴州大山里那些熟識的、命運多舛的女性。她很清楚,從觀念上,兩人并不能聊到一起,“你好像在跟一座山對話,跟一座山脈上面的小溪去交流。”
但她很喜歡小姨的真誠,不像城市里的人彼此充滿警惕。
幾杯白酒下肚,小姨向我們述說自己分手后的遭遇,被看不起,渴望愛又懼怕愛。游民女孩走出座位,注視著小姨的眼睛,“我很愛你”,她也袒露了自己原生家庭的創傷。
后來兩人離席說起私人的話,透過門縫,我看到她們互相抱在一起,兩個經歷過傷痛的人,成為彼此的安慰。
在這個荒涼沒落的鄉鎮,我好像看見飛地的邊界在融化,不是用觀念,而是情感。
“那個小屋就叫DNA”
此前一篇描寫安吉數字游民社區的小哥下,我看到一條評論,“都是些有錢人的‘消遣’!”
這顯然充滿偏見。在溪龍鄉,在那些應對媒體的“標準答案”之外,我看到了許許多多具體而真實的人生。如果一定要給這群人畫像,DNA口號“全世界有趣的人聯合在一起”,“有趣”可替換成“脫軌”,DNA游民方庭說。
北大中文系畢業的方庭,已拿到了名校的研究生項目offer。可在那條看似光明的學術道路之外,她來到DNA,線上做web3項目市場營銷。她極其文學地描述他們在安吉創造的時代和DNA這群“脫軌”的人:
社會是一輛破破爛爛運轉的蒸汽火車,外面的天氣一直灰蒙蒙的,偶爾可能會有假的太陽。火車也不知道往哪兒開。有人在黑板上寫了10,猜測可能是10個月后扭轉方向,有人猜是10個星期或者10天,可突然10、9、8、7……
上這輛火車需要付出巨額車票:戶口、房貸。有的車廂紙醉金迷,有的車廂衣衫襤褸。
很多車廂很吵,人們在聊天、吵架。有一個車廂充滿不安定的沉默,所有人都不知道說什么,甚至有些人在哭,他們已經掙扎很久了。人們也不都是望向同一個方向,很難去進行本質上的交流,只能是互相舒緩一下自己在車廂里的迷茫和痛苦。
車廂按規定,誰都不能把頭探到窗外。但那個車廂所有人都在把頭伸出去。有一天,那個車廂的人突然看到遠處一個灰撲撲的小屋,跳下車,走了一天路,到了小屋。那個小屋就叫DNA。
方庭說,她不介意在這里被房地產公司當成觀察樣本,“至少說明,大家還是愿意去參考這種生活方式,或者說把它當成一種可能性。”但她也說,DNA可能只是臨時停靠站,他們總是還要回到火車上去。
我能感受到那股往回拽的力量。3月4日,阿綠接待了父母安排的一位相親男士。對方從湖州開車1個小時趕過來,參觀了DNA后,出言道,“你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嗎?”
男士家里開工廠,自己做工程項目。他很直接地表示自己有些大男子主義,對另一半的要求就是“顧家”。他對阿綠說,你以后可以不工作,但要帶好孩子。
為了把阿綠從現在的“脫軌”生活拽回正軌,他嘗試祭出孝道,稱阿綠的父母可能因為她在外漂泊而沒有安全感。阿綠并不認可,此前她在大廠工作時,父親做手術,但她在公司加班,最后只能打順風車去醫院坐兩小時,又趕回公司上班。相反,自己現在的生活狀態,一旦父母需要時,她就能馬上陪伴在他們身邊。
聊到最后,男生問,“你現在不考慮結婚?”
“是的。”阿綠回答。
男生像是不相信這個答案,又問了一次。
“我覺得至少現在,結婚對我是個負擔。”阿綠說,其實她心里想的是,“不是和你”。她無法接受自己的人生價值被定位為“顧家”。
除了婚姻,阿綠還有更迫在眉睫的焦慮。在DNA有些日子了,她并未找到能讓自己長久沉淀的事業,她開始猶豫,春節后是否要重新回到城市工作。
在DNA,不少游民和阿綠一樣,在游與不游之間掙扎。“20多年的主流教育很難讓我擺脫(傳統的)思維模式,”一位游民說,“我還是想要在世俗上被別人認可。”很多人在DNA生活了一段時間,最終回到大城市工作,DNA的生活成了“老天的限定禮包”,沒人知道期限是多久,每天這里都在上演相聚與離別。
有一天,我和游民們一起去鎮上吃飯。店家端上一盤鍋包肉,肉被夾走后,一只蒼蠅陷進了糖漿里,好不容易掙扎出來,可是它又爬回那一攤甜蜜的黃色糖漿。
現場突然很安靜,所有游民都看著這只蒼蠅。一位游民打破沉默,“你看,曾經困住它的,它又回去了。”
或許DNA的日子真的只是一份限定禮包。我問李彥漪,如果未來溪龍鄉的項目開發成功,這里的地價和租金勢必會上漲,超出數字游民的預期和承受能力的話,怎么辦?
“在白茶原的各個角落,總有能容納他們的地方。”李彥漪覺得,一切都可以交給市場解決,也許到時候村民愿意開民宿接納游民們。這是個意料之中的答案。
尾聲
有一種冬候鳥叫山斑鳩,起飛時會發出高頻的“噗噗”聲。
安吉正處于全球候鳥遷徙“東亞-澳大利亞”路線的關鍵地帶,每年3月中旬開始,山斑鳩飛到安吉越冬,在這里短暫停留,來年3月初,它們又飛回北方。
DNA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方庭那段文學性的描述并沒有結束,她說在那個灰撲撲的小屋里,有一群人熱情地招呼你,升騰起的火焰讓人很溫暖。
3月8日,方庭招呼我去DNA。推開門,有人在有一搭沒一搭聊《追憶似水年華》,有人倚在火爐旁烤棉花糖,兩只貓在腳下亂竄,背景音樂是《請回答1988》的《雙門洞》。他們微笑著看向我,呼喚我快進來。
我知道,我和安吉的候鳥們,都經歷過那個時刻。
(感謝給予稿件幫助的所有人)
參考資料:
1《白茶原小報》, 2023
2《白茶原風物筆記》, 2023
采訪、撰文:梁靜怡
編輯:王婧祎
攝影:賈睿
視覺:aube
運營編輯:溫溫
看完關于數字游民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說的
在留言區和我們分享吧
大家都在玩的社團☞熱門大爆料☜加入社團和大家一起交流